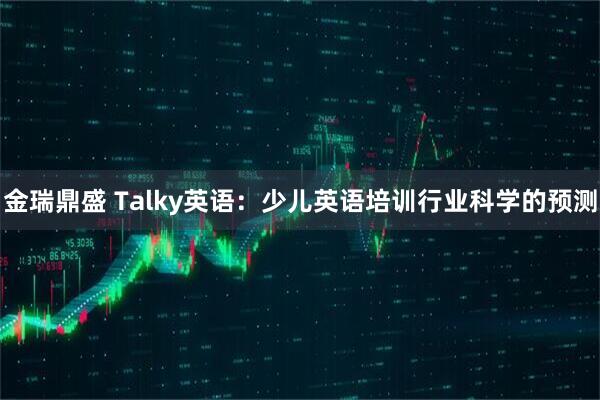日期:2025-05-29 13:35:43
道光二十三年(1843)爱策略,连日的暴雨使关中一带粮食歉收。
实在饿得不行,家住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的董春生决定出门碰碰“运气”。
他担起锄头,来到地里,希望能从田中刨出仅剩的树根或者地瓜,用以充饥。一锄头下去,却被硬物挡着。
他只能放弃工具,用手刨了起来。
不多时,一个绿锈斑斑的大铜圈和铜圈上同样长着绿锈的一对大耳,从土里露了出来。董春生不识此物,却听村里老人说过,这里常出“宝贝”。
他不敢怠慢,小心翼翼地清理掉“宝贝”上的土。很快,一件半米见方的圆形青铜器重见天日。
由于器物太大,董春生一个人搬不动,便叫来了同村人帮忙。
很快,董春生挖到古代大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随后,一位古董商人闻讯而来,花了三百两从董春生手中买走了宝贝。
由于此物是从董家村发掘的,村民皆认为是天赐“神器”,不同意商人运走。因此,关于这件宝物的归属,最后闹到了衙门。古董商重金贿赂官府,衙门遂将一众村民下狱,将宝物收归官府,由古董商悄悄运走。
清代著名收藏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碰巧见过此宝。
从宝物“敞口、双立耳、三蹄足”的外在形态来看,张石瓠很快断定宝物应为商周时期青铜鼎。
他俯身查看鼎的内部,发现鼎内壁密密麻麻写着许多铭文。经过仔细辨别和读解,他发现铭文记载的是一段历史。这尊青铜鼎的历史事实以及作鼎者信息,逐渐浮出水面。
从此,这尊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:毛公鼎。

1
提及青铜器,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墨绿色的大铜鼎。实际上,这并不是它本来的面貌。
早在1万年前,人类就从大自然中发现了一种红色的矿石:红铜。
这种矿石经过反复捶打和提炼后,可以制造出他们想要的物件。但在实际应用中,由于红铜的硬度较低,先民们又发现,单靠红铜,很难打造出最满意的作品。
于是,在不断试错中,先民们将红铜熔炼成液体,再加入铅、锡等矿物质。如此,一件最适合锻造的铜合金,大功告成。
使用它们,先人相继为自己锻造出了铜刀、铜箭等生存工具。
不过,刚炼造出来的青铜器,并不是锈迹斑斑的模样。铜合金被熔炼凝固后,呈现质感如黄金般的样态,金光璀璨。这跟我们如今看到的锈化后的墨绿色外观,相去甚远。
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——黄河流域,并不是铜产地的聚集区。铜的提炼与锻造,在产量上也无法满足先民的日常所需,因此显得十分金贵。
这些早期的“黑科技”产品被打造出来后,基本只用于祭祀祖宗,尊崇神灵,谓之“吉金”。刻在上面的铭文,自然也就成了“金文”。

然而,文明的衰落,历史的变迁,使得曾经担负神圣功能的器物全都尘封黄土之下。经过时间的淘洗,铜和土中的水汽等自然界物质发生反应。从此,那一尊尊闪煞人眼的“神器”,披上了厚厚的绿衣,成了人们追古怀今所见到的“青铜器”。

目前,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青铜器,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产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。它是一把以“单范式”工艺铸造的青铜刀。
所谓“单范式”铸造工艺,就是在平坦的泥土和石板上进行掏空,形成理想的器物外形,再将烧熔的铜液灌注其中,待其冷却凝固后,自动成型。
不过,这种“单范”的铸造工艺,到底只适合原始小家庭的自给自足。当华夏文明进入王朝时代后,这种简单的铸造工艺就被逐渐淘汰了。
大约4000年前,治水的大禹结束了部落群居生活,在中原建立起第一个王朝——夏。
新的统治秩序诞生,当然需要见证历史的信物。
夏朝建立以后,大禹随即邀请部落首领们共赴涂山大会,商讨国家大事。
为令天下臣服,大禹在涂山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以往的过失,并请求参会的首领们时刻监督他的行为,责令其改正。如此,方可匡天下正道,安万民之心。
部落首领们返回各自的地盘后,随即将辖区内的铜,悉数奉上,并宣布归附夏朝管制。
大量的铜汇聚于夏都阳城,令大禹一时头疼。后来,他想起了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“历史”,便下令将各地进献的铜悉数熔毁,分铸九鼎,以纪念夏朝一统江山的辉煌。

大禹还命人将各地的山川河流、珍禽鸟兽绘制在这些礼器上,使它们更具地方特色。而九鼎中的“中央大鼎”豫州鼎,则是大禹留给自己的王权象征。
鼎铸成后,即被视为宗庙礼器,神圣不可侵犯。
凭借此“信物”,大禹及其后人,坐稳了九州共主的宝座。
2
大禹的创举,为后世君王在“礼治”道路上作出了表率。
在玉玺出现以前爱策略,作为“礼治”的神器,九鼎就是王权、神权二元一体的绝对象征。尽管在夏禹时代,各地已持续向中州贡铜,以保障王室的生产生活所需,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关于青铜器的锻造始终处于摸索阶段。
为了制造出形制更加复杂的容器,热衷于专研高端奢侈品的贵族们开启了一场“青铜革命”。
在原单范式灌铸的基础上,一种合范技术被发明出来。
工匠们首先用陶土按器物原型雕刻成泥模,然后将调合均匀的泥土拍打成平泥片,按在泥模的外面,用力拍压,使之形成一层厚厚的“外范”。之后,将制作外范使用过的泥模,趁湿刮去一薄层,薄层的厚度即为铸造青铜爵所需的空间,再用火烤干,制成“内范”。内范做好后,将其倒置于底座之上,再将外范块置于内范周围。外范合拢后,上面有封闭的范盖,范盖上至少留下一个浇注孔。
最后,将融化的青铜溶液沿浇注孔注入,等铜液冷却后,打碎外范,掏出内范,将所铸的青铜爵取出,打磨修整即可。
利用这种办法,贵族们还相继制造出了角、斝、觚等青铜酒器。
象征九州河山、帝王权力的九鼎,后来失去踪迹,但贵族们使用的青铜器仍有迹可循。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爵,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,距今约3800-3500年,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夏代。
青铜爵造型小巧精致,极富美感,底部三足而立,中间细腰收拢,在该容器的最上方,前有“流”,后有“尾”,用爵畅饮时,嘴巴要对着“流”的部分。

不过,由于工艺复杂,散发着璀璨光芒的金属酒器,始终不适宜应用于日常生活中。待它们面世后,很快被用在各种祭祀先祖的神圣场合中。
正所谓“国家大事,在祀与戎”,礼治之外,必须辅以强有力的武功,方可使内外咸服。
夏朝建立后,战事始终没有停歇。
大禹死后,儿子启即位,禅让制彻底被世袭制所取代。从历史潮流而言,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。然而,世袭制的出现,毕竟打破了禅让制的选举传承。随后,在夏地有扈氏首领的号召下,夏王朝境内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发起对启王权继承的挑战。
启不甘示弱,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后,便以“恭行天之罚”为名兴兵,与有扈氏大战于甘。双方打得异常激烈,但史书上却仅有启兴兵前的一封诏书称:“用命,赏于祖;不用命,戮于社。”
“戮”,最早的意思即带有戈翏声的厮杀。说明在启与有扈氏作战时,青铜兵器已装配到夏军部队中。
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,与文献中记载的夏年代相近,从中可以窥探这一时期的兵戈之影。在石器时代,石制武器的缺点是磨损太快,到了青铜时代,二里头遗址中青铜戈、青铜钺和青铜箭簇等武器的出现,说明青铜器已被投入到军事领域。无论是近战,还是远射,青铜器比石器有着更强的杀伤力,而且不易损坏。
其中,二里头遗址铜戈,是中国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戈。戈,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来,这种长柄格斗兵器由戈头和戈柄共同构成,竹木质地的戈柄年久朽坏,考古发现中大多只能见到历经沧桑却依然坚韧的戈头。戈在先秦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,汉字中的“武”、“战”等都源自于戈,戈与干(盾)并称“干戈”,成为兵器的代名词。
二里头青铜戈,为长条形直内戈,前端的尖峰恰似鹰嘴般冷峻锐利,仿佛随时都能在战场上撕开敌人的防线,从中可以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技艺,遥想古代战场上的寒光闪烁。

依靠着先进的武器,启很快平定了叛乱,稳定了王朝。
实际上,夏王室并没有有直属天子的常备军队。多数时候,夏王的警卫主要由忠于他的贵族卫队组成。一旦发生战事,他就下达王命召集各地奴隶主起兵勤王。
这样便造成了夏朝王室的内乱持续不断,而外部势力也在夹缝中不断壮大。
夏朝末年,商族逆境崛起,似有灭亡夏朝、吞并天下之意。
而此时,夏朝的君主桀,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昏君。
古文献说,桀贪好女色。依靠夏朝的综合军力,他不仅消灭了许多不满其统治的小部落,更将其中的美貌女子强抢至王庭,供其淫乐。
有施氏部落的妺(mò)喜就是其中之一。
曾有诗云:“有施妺喜,眉目清兮。妆霓彩衣,袅娜飞兮。晶莹雨露,人之怜兮。”一见到这样的美女,夏桀很快就着迷了。他回宫后,立即将妺喜册为“元妃”(即夏朝的皇后),万般宠爱。
可妺喜对夏桀只有恨意,所以,无论天子对她有多好,她都毫不在意。不仅如此,自从成了元妃,她就开始筹谋颠覆夏朝的计划。
这时,有莘氏部落的厨子伊尹出现了,他是商族领袖商汤的谋士。
预感到商族对自己的威胁,夏桀在灭有施氏的同时,也着手对付崛起的商族。利用王权,夏桀将商汤软禁钧台。
为了救商汤,伊尹特地觐见了妺喜,恳求她从旁协助自己实施营救计划。
妺喜本身就有亡夏之心,再加上夏桀热爱征伐与美色,继灭有施氏之后又染指岷山氏。岷山氏效仿有施氏,向夏桀进贡美女,以求自保。在新欢面前,夏桀逐渐忘记那个他曾经信誓旦旦想给予一切的“元妃”。

国仇与家恨,使妺喜更加悲愤。
一听闻商汤、伊尹等人久怀“倒夏”之心,她欣然应允,并提出加入他们的秘密计划中。
最终,在伊尹与妺喜的合谋下,夏桀尽失民心,“兵败历山,奔南巢而死”。
3
夏朝灭亡后,“倒夏”的商汤成了商王朝的首任国君。而伊尹,则成了辅弼他的宰相。

商、夏之间的矛盾,使得他们的文化和施政方针多有不同。但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的传统,却丝毫未受影响。
1939年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(原称“司母戊鼎”),是商代青铜礼器的代表作,也是我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。在商周的礼制中,鼎是用来向祖先献上肉食的炊器。后母戊鼎重832.84千克、高133厘米、口长110厘米、口宽79厘米,鼎身呈长方形,以饕餮纹为主要纹饰,为商代后期为祭祀商王之母而铸造。铸造这样高大的青铜器,所需的金属应在1000千克以上,而且需要极大的熔炉,可见商人青铜技术的精湛。

商代初年,作为史上最著名的“厨子宰相”,伊尹有着丰富的烹调美食经验。就连给商汤分析天下大势及为政之道时,他也不忘给对方煮上一锅汤,以烹调五味为引,劝导商王救民于水火。
因此,商朝开国不久,青铜器就在祭祀功能之外,被王朝大力推广至人们的日常餐桌上。
鉴于以往生产出来的青铜器形制单一、工艺落后,商朝贵族为了安享一顿盛宴,花了不少心思对青铜器进行改造升级。他们认为,神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。所以,在使用青铜器时,自己与祖先所用的规格不能等同视之。
商朝人开始在青铜器上雕刻出不同的纹路。如祭祀先祖时,人们准备三牲太牢,就以不同的纹饰形象印刻在对应的青铜器上,寄托威严、荣贵的幻想和希望。
有意思的是,同一时期的三星堆人在祭祀上却不想运用简单的抽象化处理。他们选择了一条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青铜祭祀之道。既然是祭拜祖先,那祭品的器皿上怎能缺少祖宗形象呢?于是,参照先人模样,他们制造出了各种又高又大,方脸凸目的青铜人像。

对于日常吃喝玩乐,商朝人有更细致的美学实践。
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,到了商朝,粮食第一次出现剩余。粮食的丰富,推动了商代酿酒工艺的发展。祭祀需要用酒,平时宴飨也需要用酒,故商朝对青铜器在餐饮上的应用,首先立足于酒器革新。
他们发现,平常用于祭祀的酒爵,爵身扁平,即便设有三角支撑的杯足,很多时候也容易在祭祀大典上倾倒,引发众神之怒,责怪在位君王。
所以,商朝工匠们干脆将酒爵设计成底部稳实的觥。一来,觥体宽阔可以注入更多的酒。二来觥圆润的身躯,不至于在风中凌乱。
从商父乙觥中可以发现这种青铜酒器的实用美学。父乙觥由盖、身、鋬和圈足等几部分组成,觥盖前端有一兽首猛然抬头,双角凌厉上翘,铜铸的双目保持着圆睁的威严;再看觥体的周身,凤纹飘逸,振翅欲飞,勾勒出动静交织的神话画面。

商人大量饮酒固然与风俗习惯有关,但酒品的大量消耗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的酿酒工艺尚未成熟。为满足商人大量饮酒的需求,工匠们又相继发明了尊、罍等大型容酒器。
尊,作为一种大中型的盛酒器,有圆腹或方腹的器形,口径较大,主要用来存放酒。
诞生于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——四羊方尊,为我们还原了尊的精美形制。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,呈方形器身、方口、长颈、高圈足,高58.3厘米,口长52.4厘米,圆雕、浮雕、线雕集于一器,四边装饰有蕉叶纹、三角夔纹和兽面纹。四羊方尊最生动的部分,当属其肩腹部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山羊,羊首花纹精丽、伸出器外,又与器身有机地结合为一体,大大丰富了尊的造型,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。
罍,也是一种盛酒的容器,具有小口、广肩、深腹、圈足的特征,带有盖子。
商皿方罍,号称青铜器中的“方罍之王”。皿方罍,通高 84.8 厘米,器身高 63.6 厘米,因其为方形器皿,以及器口铭文“皿而全作父己尊彝”而得名。皿方罍以云雷纹为底,饰有兽面纹、夔龙纹、凤鸟纹,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,正面腹部下方有一个兽首的鋬(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部分),器型硕大,雄浑庄重。这件青铜器可谓命运多舛,1922年出土后,器身与器盖一度长期分离,分别在海外和国内流传,直到2014年才在各界的努力下完成合体,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。

与早先出现的爵不同,尊、罍等都考虑到了酒体贮藏。为避免过多的酒精挥发,设计者们通通为它们量身定做了盖子,尽可能降低容器中的酒与空气接触。
参照祭祀,商代工匠又在尊、爵的切换中,发明出分酒器“壶”“卣”等。与大型容酒器类似,它们的瓶口也是带盖的。同时,为方便贵族们在酒桌上互相“满上”,设计者还专门以铸焊的方式在瓶身上,加了道“横梁”,便于贵族们拿起。
河南辉县出土的祖辛卣,为商代青铜卣中的典型代表。古朴典雅的造型与华美繁复的纹饰熔于一炉,器口与盖以子母扣严密合缝,鼓腹下垂,圈足稳健。盖顶置菌状钮,盖缘与器身对应伸出四条扉棱,构建出精美绝伦的立体轮廓,腹部高浮雕的鸟眦目凝视,营造出神秘威严的氛围。盖内与器底均铸有“祖辛”二字铭文,这是商代其中一任君主的称号。

防止有人不胜酒力,提前喝趴下,贵族们还特地找人设计了一种用于调和酒味的器皿——“盉”。青铜盉是一种调酒器,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,主要用来温酒或以水调和酒水的浓淡,其特点是圆口、深腹、三足,一般带有细长的流管。
自此,商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猛灌酒了。
有了美酒相伴,商代贵族们的餐桌又怎能少得了高级肉食?
在农业耕作水平发展的背景下,商朝的畜牧业也迎来了一次发展高峰。甲骨文中,人们形象地将猪圈写作“圂”,把圈养牛写作“牢”。

而通过人类驯化的猪、牛、羊、马、犬、鸡等六畜,除了供给奴隶主驱使以及祭祀祖先外,大部分都成了主人家补充营养和体力的主要来源。
这时候,有一口好锅,对商代贵族而言,便显得十分重要。
作为调和五味的“宝器”,鼎在商代除了日常祭祀,就是奴隶主家中最大口径的锅。由于体型巨大,多数时候奴隶主会沿用其祭祀的功能,在鼎中烹饪大型肉食。
不过,大火易将铜合金的锡析出,致使青铜鼎结构不稳,因此,更多情况下,华丽的青铜鼎只能用来盛放肉食,以彰显主人家的高贵。

为了吃上一口热饭,奴隶主斥巨资设计了一套青铜炊具“甗”。它分上下两部分,上半层可用于盛放食物,名叫“甑”。甑的底部有一层满布小孔的箅子。下层是“鬲”,用于盛水。每只甗的底部,还如鼎一般设置多足,可将它们架于火上烤。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蒸锅。

“食而能知其味”,为了给贵族更直观的视觉和味觉享受,工匠们还特地在各式青铜器外立面中加入云雷、夔龙等纹饰,除了表明青铜器内的食物原型外,更彰显了主人家的身份和地位。
可惜,在如此品类繁多的饮食形制中,商朝还是亡了。
与夏朝相似,商朝也亡于外患——上古周氏族崛起。
周人原本是商朝边陲的一个小部落。因戎狄入侵,领袖古公亶父遂将部落迁至周原(今陕西岐山北)。
抵达西岐后,周人开始“脱戎俗,筑邑定居”,学习商朝的农业文明。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,古公亶父及其后人大力与当地羌人联姻,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。

古公亶父去世后,幼子季历即位。季历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,他在位期间,师承其父遗嘱,在当地大兴水利,发展农业,推行仁义,富民强军。不多时,周就成为商朝实力最强的外夷部落。
周的强大,引起了商朝的注意。
为了遏制周氏族的发展,商王室不断利用周族去跟外来戎狄硬碰硬,打算通过战争消耗周部族的有生力量。
不料,通过“以战养战”的方式,季历率周人愈战愈强,商王文丁亦不得不对季历一赏再赏。几轮下来,季历成了商王室钦命的“商朝西部众诸侯之长”。
周室借消灭戎狄,大力扩充自家军力的举动,终于引起了商王文丁的恐慌。借重赏季历之机,文丁将其调入殷墟,伺机命人暗杀。
季历的突然死亡,并没有暂缓周人的扩张进程。季历之子姬昌,也就是《封神演义》中受人尊敬的西伯侯,在即位后秉承父、祖遗志,周氏大力发展军备。到了商纣王时代,他们的势力范围已推进至河洛地区。
这里是商朝的发源地,周室的崛起,自然引起商纣王的高度重视。
效仿祖父文丁,商纣王“杀周太子历,囚文王昌”,周人与商王室的矛盾最终公开化。
秦安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